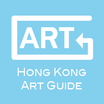專訪 interview
HONG KONG ART GUIDE
專訪-香港年輕水墨藝術家熊輝
2013年3月2日
水墨藝術通常都會令人聯想起中國的傳統,多取材於山水、花鳥、梅蘭竹菊和木石等。但是,當水墨藝術遇上這個八十後青年藝術家熊輝後,便獲得新生命。一幅幅像腦素描又像X光片的畫作,帶領觀眾用一個全新的角度審視水墨畫,同時亦啟發大家思考著生命的變奏。
「變奏-熊輝水墨作品展」現正在Fabrik Gallery舉行中,3月12日結束。我們很榮幸透過Fabrik Gallery 邀請到熊輝作一個專訪,跟大家分享他的藝術生涯以及創作過程。
HKAG: 何時開始接觸中國水墨藝術?
熊輝: 從小就每天看見父親在家中的畫室作畫。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趁父親不在家,便偷偷走進畫室裹。牆上掛著一幅直幅的山水畫,對兒時的我來說很巨大,好像另一個世界似的。看著看著,我突然發現瀑布下竟然沒有石頭,那種找到了「空隙」的感覺很興奮,於是我便拿起毛筆,模仿地畫了一塊似模似樣的石頭,高興了很久。那是我首次感受到創作的喜悅。
HKAG:為什麼選擇中國水墨藝術作為你的藝術創作的媒介?
熊輝:「水墨」是我的創作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反應點。曾有一段長時間,因為自身的成長環境:念的是英文中學、聽的是西方流行音樂、手握的是啫喱筆,加上「水墨」就猶如是「父親」的代名詞,我偏好西方媒介的創作。甚至帶一種抗拒的心態對待「水墨」。其後漸漸發現排除不同媒介在物料上的差異所來的新鮮感和沖擊外,其實核心裹一些創作的喜好和心態、驚人地與一些「水墨」的概念接近。這使我很震驚。也逼使我面對自身和傳統、水墨與當代藝術的關係。回想起那時抗拒的心態,除了帶著如害怕被閹割般的恐懼外,其實也以一種逃避的心態來回避當中的割裂和矛盾。這驅使我返回瀑布前,思考瀑布的「留白」背後到底是石頭還是水簾洞,倒讓我重新找到一個立足的「空隙」。
HKAG:聽聞你的父親也是藝術家有没有從他身上學到什麼?
熊輝:父親對我的影響很大。他向我證明了只要堅信自己的信念、按自己的步伐,就能一直走下去。
HKAG:你這次展覧中的一系列作品《變》是想表達什麼?可否簡述?
創作這幅作品《變》之三從好像ー個圓形胚胎慢慢衍生不同動物形態的作品繪畫時最困難是什麼?畫了多久才完成?
熊輝:當中有一個核心的思想,就是反思自身的源由和意義。對我來說,那不僅是題材性的表現,當中也包含一些價值的取捨與重新創造。困難是《變》系列為了把生長的過程和痕跡一步步累積和記錄,是結合宣紙的特性以一疊多摺的方法進行創作,當中所運用到水墨滲化的技術,是由不斷進行實驗而獨創的,需要高度控制和克制的能力。而把原來一氣呵成的步驟分割為多層,按層繪畫,所花的精力和時間也以倍數計。
HKAG:這次展覧中你認為那幅作品在技巧上是最困難的?
熊輝:兩個系列、《變》和《淋漓》的創作模式就像縱向和橫向的分別。《淋漓》一系列的技巧難度是大面積的滲化,是由逐點點上再以水化開,如煙花消散。期間宣紙需要不停保持濕潤,並以長時間、一氣呵成的方式創作。
HKAG:讓你毎次創作的最大的動力是什麼?
熊輝:對我來說,創作就像照鏡。第一次照鏡是看自己的模樣,第二次時就自然會留意自己和昨日有什麼差別。這是不能忽視的本能,也是最基本。
HKAG:你認為一個藝術家最基本需要什麼特質?
熊輝:懷疑、反思的能力和判斷力。
HKAG:接下來你有什麼創作計劃?
熊輝:以《變》一系列為基調繼續進行探索和實驗,並進行較大型的創作。
我們期待看見熊輝將來的作品更見突破 !
關於熊輝:
1988年生於香港,熊輝自幼對繪畫產生濃厚興趣。透過中西媒介不斷實驗、探索,獨創出滲化技法,以獨特的形式重新演釋水墨。
2011年,熊輝榮獲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展 ― 丁衍庸藝術創作獎,2012 年再獲得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展 ― 王無邪現代水墨獎。他的作品「變」更晉身香港年輕藝術家獎 2012 十強。
「變奏-熊輝水墨作品展」現正在Fabrik Gallery舉行中,3月12日結束。我們很榮幸透過Fabrik Gallery 邀請到熊輝作一個專訪,跟大家分享他的藝術生涯以及創作過程。
HKAG: 何時開始接觸中國水墨藝術?
熊輝: 從小就每天看見父親在家中的畫室作畫。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趁父親不在家,便偷偷走進畫室裹。牆上掛著一幅直幅的山水畫,對兒時的我來說很巨大,好像另一個世界似的。看著看著,我突然發現瀑布下竟然沒有石頭,那種找到了「空隙」的感覺很興奮,於是我便拿起毛筆,模仿地畫了一塊似模似樣的石頭,高興了很久。那是我首次感受到創作的喜悅。
HKAG:為什麼選擇中國水墨藝術作為你的藝術創作的媒介?
熊輝:「水墨」是我的創作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反應點。曾有一段長時間,因為自身的成長環境:念的是英文中學、聽的是西方流行音樂、手握的是啫喱筆,加上「水墨」就猶如是「父親」的代名詞,我偏好西方媒介的創作。甚至帶一種抗拒的心態對待「水墨」。其後漸漸發現排除不同媒介在物料上的差異所來的新鮮感和沖擊外,其實核心裹一些創作的喜好和心態、驚人地與一些「水墨」的概念接近。這使我很震驚。也逼使我面對自身和傳統、水墨與當代藝術的關係。回想起那時抗拒的心態,除了帶著如害怕被閹割般的恐懼外,其實也以一種逃避的心態來回避當中的割裂和矛盾。這驅使我返回瀑布前,思考瀑布的「留白」背後到底是石頭還是水簾洞,倒讓我重新找到一個立足的「空隙」。
HKAG:聽聞你的父親也是藝術家有没有從他身上學到什麼?
熊輝:父親對我的影響很大。他向我證明了只要堅信自己的信念、按自己的步伐,就能一直走下去。
HKAG:你這次展覧中的一系列作品《變》是想表達什麼?可否簡述?
創作這幅作品《變》之三從好像ー個圓形胚胎慢慢衍生不同動物形態的作品繪畫時最困難是什麼?畫了多久才完成?
熊輝:當中有一個核心的思想,就是反思自身的源由和意義。對我來說,那不僅是題材性的表現,當中也包含一些價值的取捨與重新創造。困難是《變》系列為了把生長的過程和痕跡一步步累積和記錄,是結合宣紙的特性以一疊多摺的方法進行創作,當中所運用到水墨滲化的技術,是由不斷進行實驗而獨創的,需要高度控制和克制的能力。而把原來一氣呵成的步驟分割為多層,按層繪畫,所花的精力和時間也以倍數計。
HKAG:這次展覧中你認為那幅作品在技巧上是最困難的?
熊輝:兩個系列、《變》和《淋漓》的創作模式就像縱向和橫向的分別。《淋漓》一系列的技巧難度是大面積的滲化,是由逐點點上再以水化開,如煙花消散。期間宣紙需要不停保持濕潤,並以長時間、一氣呵成的方式創作。
HKAG:讓你毎次創作的最大的動力是什麼?
熊輝:對我來說,創作就像照鏡。第一次照鏡是看自己的模樣,第二次時就自然會留意自己和昨日有什麼差別。這是不能忽視的本能,也是最基本。
HKAG:你認為一個藝術家最基本需要什麼特質?
熊輝:懷疑、反思的能力和判斷力。
HKAG:接下來你有什麼創作計劃?
熊輝:以《變》一系列為基調繼續進行探索和實驗,並進行較大型的創作。
我們期待看見熊輝將來的作品更見突破 !
關於熊輝:
1988年生於香港,熊輝自幼對繪畫產生濃厚興趣。透過中西媒介不斷實驗、探索,獨創出滲化技法,以獨特的形式重新演釋水墨。
2011年,熊輝榮獲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展 ― 丁衍庸藝術創作獎,2012 年再獲得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展 ― 王無邪現代水墨獎。他的作品「變」更晉身香港年輕藝術家獎 2012 十強。